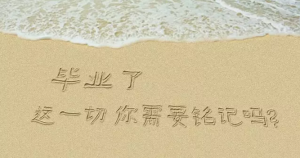
赵小姐来深圳了。
年前我就知道她有可能会来深圳,但最近并没什么信儿,等她人都到这两天了,突然发信息给我,“我到深圳”。搞什么?这么突然,我一时有点气恼。不过想想也好,10分钟一班的和谐号把广州和深圳连得亲亲密密,我在广州也不至于显得太孤单。
赵小姐做事一向都是这么突然,初中的时候,我们还在西北大漠的沙尘暴中挣扎。植树节全校照例去城郊的荒滩植树,其实就是挖坑,其实连挖坑也不是,貌似是市政叫来机器挖坑,结果挖多了,让我们去人工给填上。我也想不通为什么我市年年都要搞出这样一些脱了裤子放屁的事,结果导致了一个少女在班主任心目中地位的滑铁卢。
现在事情看起来很简单,就是赵小姐的大姨妈突然来访,且来势汹汹毫不留情,在这片一望无际的沙滩里,赵小姐孤立无援,于是决定回家。问题在于,她走的突然,没有告诉任何人。临走点人头的时候,班主任急了,把我们几个狐朋狗友挨个拷问了一遍,可我们真的无辜。
这场审查持续到第二天上课,瘦瘦小小的老王又是嘶喊又是甩头,稀稀拉拉的马尾抽出响儿来。我们一圈姐们儿在大家的注视中站着,实在不知道说啥,这真的不是早有预谋,这真的不是协同作案,这真的不是调虎离山。老王生气倒不光是因为赵小姐丢了,当我们在大太阳下焦急的等待她时,一个女孩消无声息的晕倒了。她叫孙月然,她在荒地里躺了很久,她让举目四望一片荒凉的老王几欲发狂。朔风野大,回不了家,大爷板车,伸出援手。
其实事情到此还是很圆满的,晕姑娘没啥大碍,赵小姐也平安回来了,我们这帮熊孩子都还健在,只是老王心底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,她被赵小姐深深的伤害了,赵小姐是这么对我说的,“你没发现吗?老王从此就不待见我了”。
屁,她的初中风生水起,用她的话说,“虽然我初中长了一脸青春痘,可学校所有的大型活动都是我主持的,哈哈,哈哈哈哈!”
我可不是神经脆弱的老王,知道她来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淡定,我说“好”,然后又忍不住问了一句“住的地方找到了?”,“嗯”,“你男人给找的?”“嗯”“我去看你!”“等你”。
然后我就因为各种不可抗力一直没有去找她,但她总是显得很淡定,没有着急没有催我,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形式的恐慌,我想有她男朋友在,一切都不是问题。这种假象持续了快一个月,在我生日前两天,凌晨一点我正开夜车赶工,突然收到她一条微信语音,“我睡醒了,就我一个人,一个人···”她在哭,我就听清了这一句话。
她又在哭,这姑娘在我面前哭的次数不少,可哭的原因就那么几种。一是爸,二是妈,三是爸妈,四是奶奶,或许有五吧,那就是她自己。这个一二三四五,让她在二十几年的人生里流了别人大半辈子的眼泪,尤其是我这种不怎么哭的人。可她哭过就放下了恐惧,我只会把恐惧深深埋在心底,所以我敬她是条汉子,硬是挺着这些年没说。
记得在她高一搬的第三个家里,卧室挂了一副画,不,是一条横幅。她在上面写着“不哭,眼泪是珍珠”,还画了不少唯美主义的花花草草,要真是这样,她现在就应该是继陈丽华之后的第二富婆,江湖人称南海赵珍珠。
赵珍珠的新贝壳着实不大。晚上十点,我从广州赶到深圳宝安区,等我穿过工地,挤上公交,终于到达滢水山庄时,确发现这里就是个小石牌。石牌村,广州最大的城中村,4万多平方公里住了将近30万人,以密密麻麻的接吻楼和凌晨两点后的站街女闻名。公车甜美报站,“滢水山庄到了”,我隔着玻璃看到了赵小姐和她男友陆建,还好,她没瘦,尤其是胸。在我们小闺蜜群里,胸胸是对她最亲密的称呼。
见面,拥抱,并用余光扫描她男友,我跟着他俩穿过几条嘈杂的小巷,沿途路边摊和广场舞的热闹顿时让我放心不少。顺着昏暗的楼梯向上,扭开嘎吱乱响的铁门,黑压压的屋里一支小蜡烛顽强的燃烧着,赵小姐和男友、室友给我唱起生日歌。
啊,又是这么突然,人家鼻子酸酸的,讨厌。离家以来,我从不过生日。
赵小姐亲自下厨,我们吃着火锅唱着歌,好不快活。可是我的目光总是放不展,小小的门厅,一张桌就满满当当,沙发让给我和室友坐,她和男友坐在两个大桶上。
陆建客气地照顾着我,饭后温顺地洗锅洗碗,告别离开。这让我不能想象,这还是我从赵小姐嘴里听说的那个愤而泪下的陆建吗?
上个秋天,陆建所在的公司去赵小姐的大学招生,平淡无奇的相遇在春节发酵。赵小姐整天泡在QQ上,用讲“打豆豆”的老本行主动出击,陆建则以“五个边最多有几个交点”完美接招,最终俩人情定情人节。开学后,赵小姐返校,没过多久陆建就做了长途火车去见她,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。
第二次见面的第二天,赵小姐忍不住对他说,“我觉得我们不合适,要不然还是当朋友吧”。听闻此言,而立之年的陆建,当即留下了悲愤交加的眼泪。

“他哭的很愤怒吗?”
“嗯哪!可能是觉得我羞辱了他。”
“那你咋回答的啊?”
“还能咋说啊,吓了我一跳,就说那先处着呗。”
后来七零八碎的乱问一通,事情前后连起来应该是这样的。陆建不远万里从深圳去长沙看她,接了车在公交上,她就已经幸福的依偎在陆建的怀里打起了瞌睡。两人重走了当年我俩的经典路线,游衡山看日出,中间上演了流眼泪的小插曲。
“你咋就突然想起来跟他摊牌了?”
“当时我俩没出门,在宾馆看我导的话剧,他感觉看得特烦躁,特没意思,以前他可不是这么说的啊,他说对话剧很感兴趣啊。”赵小姐的戏可是在湖南大剧院卖过票的,座无虚席。
“那你就分啊?”
“没啊,我不就说说嘛!”
幼稚,我心想,不就一个话剧。可相处了一天,我深刻的体会到了我是90后,跟陆建能交流的话题实在不多,也顿时理解了赵小姐为什么第二天就想恩断义绝。可他一路照顾我们三个女生吃喝玩乐,任我们开各种没节操无下限他听不懂的玩笑都嘿嘿乐着配合,我又顿时明白了赵小姐为什么跟他好到现在。胸胸你就嘴硬吧,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占领了你的精神高地。一个女人,再傲些,也受不了一个男人那样对她好。
好在她的卧室宽敞明亮,盛得下一张宽阔的书桌。喊我点上茉莉花精油灯,卧谈继续进行。赵小姐一定是那种剩一口水也会留半口抹头发的人,蜗居千里之外,香照熏,花照养。搬家的时候,大包小包的,她还从长沙抱来了一盆快开的栀子花,“马上就要开了,留下了怎么办啊!”。
怎么办?我对一切除我以外活物的态度都是: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我还养它?赵小姐不是,她有时候会像圣母一样播撒慈爱,比如喂她家门口又凶又丑的肥猫。有时候她又心狠的干脆利落,就像不幸中招的陆建。
原创文章,作者:王乐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《大学毕业纪念小说:赵小姐(一) 夜袭深圳》https://tianfangyantan.com/articles/1618









